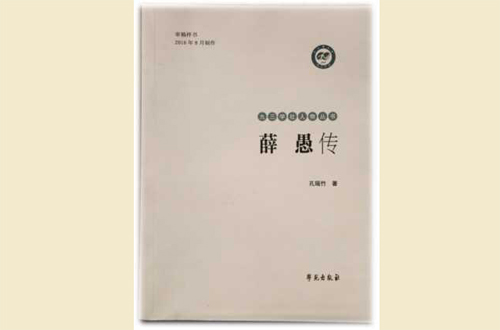
|
|
1988年1月17日,一位高龄病患在北医病世。北医党委集体违背了这位病人的遗愿,未将他的遗体进行解剖——他们通过最后的“忤逆”,表达了自己对这位老者最深的敬意。 这位逝者,就是薛愚。他是我国药学事业和药学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也是我们九三人的一位杰出榜样。 薛愚的学生王广生、宋之琪夫妇执笔为薛愚写过一本自传叫《坎坷少年时》——“坎坷”这个词可以说贯穿薛愚的一生。 从学成归国那一刻开始,薛愚就开始书写他那“惨不忍睹”的工作简历:进入河南大学执教,被河南大学解聘;进入西北农专执教,被西北农专解聘;进入国立药专执教,被国立药专解聘;进入齐鲁大学执教,被齐鲁大学解聘;直到进入北大医学院执教,以为终于可以“尘埃落定”了,谁知因为“右派”问题被“闲置”近二十年。 但薛愚在这样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中完成了许多难以想象的重要工作:撰写了中国第一部药学专业教科书、第一部化学实验教程、第一部医科专业有机化学教科书等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着,在保护、促进我国中药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编撰了第一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薛愚还将药学院系的建设工作做到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他在西北农专时,便在西北农专创建了农化系;在齐鲁大学时,便在齐鲁大学创建了药学系;在旧中国仅有的两所药学院校之一国立药专受动荡时局所迫而关门时,他重建了国立药专一力促成药专复员;他在北大医学院时,北京医学院自北京大学独立出来,薛愚又成为北医药学院第一任院长也是终身名誉院长。 薛愚建系的速度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项容易的工作,但当中的曲折外人难以想象。比如国立药专的复员,当时国民政府是想要借抗战裁撤药专。在复员讨论会上,军医署署长强硬地指出“药专无复员之必要”,称药学是“房前屋后、奶奶婆婆就可以搞定的事情”,薛愚历陈药学发展与国家安危的关联,驳得对方哑口无言;政府代表又转而“建议”药专“宜留在重庆不必迁复南京”,希望药专在重庆自生自灭。薛愚当即决定“先下手为强”,会后立即动用私人关系敲定了药专迁复南京事宜。谁知回到南京,国民政府又说要“一切从简”,并不拨给药专经费,薛愚又带领药专勒紧裤腰带“苟延残喘”挺到了新中国成立,改组成为了南京药科大学。解放后的北医药学系也是在薛愚的不懈努力下改系建院,一步一步发展壮大。没有校舍,薛愚便上书毛主席,与中央军委“抢地”,为药学系争取了霍家花园的基地。后来霍家花园的校舍又被其他院系“征用”,薛愚又到教育部“要说法”,争来了搬迁时药学系优先选址的待遇。 还有一件事上,薛愚也是诠释了“上蹿下跳”、“八面玲珑”,就是营救共产党人马适安。薛愚获悉马适安被捕时马适安已经被关押三年之久——三年来中共地下党方面也是苦于营救无门。薛愚了解到当时冯玉祥因北京事变之故被蒋介石雪藏,正郁郁不得志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故薛愚找到冯玉祥旧部王子元,王子元正有意笼络薛愚,故热心帮忙联络,获得了冯将军的亲笔信——但可惜信至陆军监狱却石沉大海。薛愚以为是王子元面子不够大,又辗转找到冯玉祥私人医生陈崇寿——陈崇寿还是冯玉祥“替身”,与冯玉祥关系更近一层。于是薛愚通过陈崇寿要来冯将军第二封语气更为强硬的亲笔信,才迫使陆军监狱放人。薛愚自己屡屡被解雇,从来不去“公关”,但每当为了学校的事情、为了救人的事情,薛愚总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公关”能力。 说到薛愚屡屡被解雇,没有一次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被解聘。解放前,他是因为支持学生运动、配合地下党工作、抵抗三青团扩张才屡屡得罪当局而被打压。解放后,薛愚被划成右派、解除职务,也是因为他替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基层药工和药学专业的学生讨公道、鸣不平,结果直接导致自己蒙冤,导致自己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不能发表、许多重要建议不被采纳——在今天许多人看来,这是不值得的,是有些傻的——的确,在风雨不停袭来的几十年当中,薛愚仿佛一直也没学会明哲保身,以至于正如王广生教授所说的那样,当我们今天想要纪念他一下,都找不到一两个能够代表他卓越贡献的完全属于他个人的成果。 但薛愚绝不是一个生性暴躁鲁莽的人,因为他在最为艰难的岁月中仍然说:“环境是艰难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是我为中国药学事业奋斗的决心是抑制不了的。至于我个人,则像疾风下的劲草,虽然风雨不停地袭来,但依然生活在人间。” 在整个蒙冤岁月中,薛愚没有牵连任何无辜的人,甚至因为不愿眼见年轻学者毁掉学术前途,还挺身而出替他们扛下了不少罪名,为当时北医的一批年轻学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当多年后这些受到庇护的学生、学者表达自己对薛愚先生的感激之情时,他只说是“凡人做了一点善事罢了”。 薛愚在抉择中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指引,可能比他在学术上给予的指导更加珍贵。这种精神,我认为是一种不避祸福的坚持——九三人一脉相承的对真理、对科学、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很难去归纳究竟什么是“九三精神”,它在每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可能都不一样,于有些人是无私奉献,于有些人是求真创新,表现在薛愚身上,我认为就是“坚持”。 其实薛愚有很多机会可以放弃。在法国读完书他可以直接留在当地工作,但他没有。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可以避开半死不活的边缘学科,但他没有。在第一次被解聘的时候他就可以调整自己的作风不再管进步学生的那些“破事儿”,但他没有。在创建药学系被各方阻挠的时候他可以隔岸观火安稳地当他的化学教授,但他没有。在向全国人大提交考察报告的时候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没有。在被雪藏后他可以离开祖国安度晚年或者抱着怨恨对抗政府。但他都没有,直到临终时他仍然在病床上写着对药学教育的相关建议。 因为薛愚在教会学校长大,不妨引用一些宗教语言。马太福音中说:上帝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毁灭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恒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上帝叫我们要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地去生活。 beat365在线登录app_365彩票app下载不了_365bet品牌中文网其实不论是自由、民主、科学、教育,哪一个不是这样一道道窄小、艰难的门呢?是无数像薛愚这样的前辈、先贤,他们穷尽了一生的努力,以一己之力稍稍拓宽了那道门、那条路。 2015年,我开始着手撰写《薛愚传》,2017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当我完成这本《薛愚传》回过头来想: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社史、研究先贤。不是我们想要以继承者的姿态躺在他们的功劳簿上接受敬仰和崇拜,而是我们需要从他们的一言一行和一次次的抉择中思考,思考当如何在逆境中坚守自我、坚守真理,不负使命、不负生命。 |